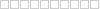□ 孙怀平
读书,看到这样一段话:墙角种满南天竺,麻袋一上一下地摔,形成棕黄色气流,让南天竺下巴尖尖的叶子咬牙切齿般抖动。祖母青灰色衣裳黑布鞋,在气流和南天竺中间,好像刻出来的版画——这么朴素的人物,我想不出谁能够刻出。祖母摔芋头的画面,如子弹击中了我。记得,奶奶在世时,也曾这样摔过芋头。
散步,路过一片菜地,一畦芋头绿叶田田。一老妇在为芋头浇水,水在芋叶上滴溜溜打着转,迟迟不肯落下。这样的画面很是眼熟,以前家里的菜园子里,母亲也种过芋头的。芋头喜水,每年春天,挑小河边的一块地下种,这样浇水方便。夏天,母亲早晚都要给芋头浇水,长柄的水舀从小河里舀上水,长柄一横,水呈扇面形均匀地洒在芋叶上,天空落雨般自然。这样的浇水技术,我掌握不了。我浇水,兜头倒下,总是吓芋头一跳。
芋头的叶子跟荷叶相似,初见的人,也许会把芋叶当成荷叶。细看,两者并不相同。荷叶是圆形的,芋叶多是椭圆形的。荷叶出水亭亭而立,芋叶多是斜立在茎上,像姑娘肩头斜打的雨伞。尽管不同,芋叶的气质一点不输荷叶。夏天,芋叶长得极快,半人多高的绿茎挑着肥大的叶子,在风中轻轻摇摆,有着天高云淡的远意,那风韵也是可入诗、入画的。
女友用水培芋头做盆景,盛夏,这案头的一钵碧绿,有着荷样的清新和清凉。
不过,芋头毕竟不靠颜值取胜,芋叶的美丽只是“顺带一笔”,最吸引人的是芋头。芋头的样貌很普通,棕色的外皮上还有棕色的毛,俗称“毛芋头”,像极了披着蓑衣的老农,不过,沧桑的外表下裹着的是粉香绵糯的身子。
秋风渐凉,芋头也熟了。从土里挖出来,洗干净,清水煮熟,剥皮蘸白糖吃,就很美味,这是芋头最家常的吃法。《西游记》八十二回里,陷空山无底洞的金鼻白毛老鼠精曾置办了一桌菜来招待唐僧,其中就有“烂煨芋头糖拌着”。
八大山人朱耷有首名《题芋》的题画诗:洪崖老夫煨榾柮,拨尽寒灰手加额。是谁敲破雪中门,愿举蹲鸱以捧客(蹲鸱,芋头的别称,因大芋头的形状像伏蹲的鹞鹰)。寒冷的冬天,屋外白雪飘飘。屋内,画家用短小的木材棒烤着芋头,拨火时,手覆额头以防烟灰落入眼中。谁会来敲这大雪封住的门呢?即使有客来访,也只能以果腹的芋头尽待客之道了。诗中弥漫的困顿凄寒令人感伤,不过这雪中拨碳烤芋的场景,让我想起小时候烤芋头的情景。
年少时,物质贫乏,芋头是难得的美味,常在帮助母亲烧火做饭时,埋些芋头在灶膛灰里,芋头小,容易熟,闷熟的芋头别有风味,有特别的焦香。也曾跟小伙伴,在野外烤芋头吃。现在想来,那跪在地上撅着屁股吹火的情景如在眼前。有时风吹过,烟灰落入眼中,呛出了泪水,和着烟灰,脸变成了花猫脸。有的吃,什么也顾不上了。成年以后,我再没有过为了吃而不管不顾的了,倒不是不愁吃的了,更多的,是少了那份热烈单纯的情怀。它跟那些甜蜜绵长的滋味,一起消失在时间的长河里。
其实,除了水煮芋头、火烤芋头,芋头的吃法可谓花样繁多。粉蒸芋头、芋头红烧肉、芋头蒸排骨、芋头炖鱼头……不过,大多需要去皮。芋头的皮中含有碱性很强的黏液——草酸碱,对皮肤有很强的刺激作用,会引起皮肤瘙痒。所以芋头好吃,皮难去。小时候,怕刀划伤手,我常拿块碎瓷片刮,刮完芋头,手指又疼又痒,忙洗手,并到灶旁烤烤。奶奶会用袋子装些芋头,拿起袋子上下抖动,或在地上摔打。这样处理过的芋头,皮的确好剥些。
饭店吃饭,上来一大盘“五谷丰登”,客人们纷纷把筷子伸向芋头、山芋、花生、玉米……我剥了一个芋头,玉色的芋肉,在灯下有温润的光。莫名,想起《红楼梦》中黛玉的诗句“煮芋成新赏”,轻盈的雪花如煮芋一般明媚,当真是洁白如“芋”、秀色可餐呢,好有新意。不过,她可否懂得,宝玉讲的那个小老鼠偷香芋的故事。那一句“我说你们没见过世面,只认得这果子是香芋,却不知盐课林老爷的小姐才是真正的香玉呢。”这香芋里又有着多少欲语还休的深情。
(责任编辑:凌薇)
版权声明:凡注明来源“0517网”的作品均为本网原创作品,未经授权,请勿转载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