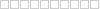岁月渐长,开始忘记很多东西,但是也会记牢一些片段。
忘记的看似很重要,而记得的片段貌似破碎、隐秘和闪烁,像失眠的深夜里,心头的沉渣泛起。
细究起来,这些片段充满关联和指向性,像某一段过去或者某一个事件的标题。等你抽丝剥茧,从容温习。
比如,一株细瘦的白兰花。
我总以为那是梦境里反复出现的画面,或者源于若干年前在江南读书,街头飘过的蓝布青衫的吴侬软语:姑娘,白兰花要伐?
直到有一天,她迎面向我走来。面容衰老,身形松弛,衣着亦不甚讲究,手里提着黄瓜西红柿等几样蔬菜。只有一双眼睛依稀是当年模样,毛茸茸的睫毛,活泼泼的双眼皮。终于,那一刻记忆自动连缀了起来,红砖平房,细瘦的白兰花树,和她。
工厂大门西侧是一片家属区,几排式样刻板统一的红砖平房,看上去有些年代了。家家门前是条半尺宽的阴沟,终日沉滞着暗沉的脏水,盛夏时不免散发出挥之不去的馊臭。红砖平房外面看起来都一样鄙旧,但条件好的人家陆续重新翻盖装修过了。老式的木质窗户换成铝合金的,水泥窗台上晒着小米椒、蒜头和几头玉米棒。院门外新搭了湛蓝的挡雨棚。
她姓陶,大家都叫她陶子。陶子家更为讲究,卧室铺着木地板,整套的水曲柳家具,小小院子里是平整的水泥地面和井台,一株绿盈盈的白兰花树。
夏天,白兰花开了。师傅们爱到陶阿姨家摘花戴。
早晨七点半上班,收拾整理一下案头资料和表格,泡杯茶喝两口。师傅们就领着我们慢吞吞地走出行政楼,开始到车间例行日常检查。进厂门前,先弯到陶阿姨家。已经是太阳当头照的八九点钟了,她才起床,梳洗或吃早饭。第一次见到她,她就坐在梳妆台前,落寞地扑着粉,抹上口红,白净细腻的脸庞,波光穿梭,眼神黑亮。一袭黑底碎花的真丝长裙,露出少女般纤细的小腿和脚踝。这是个能发光的女子。
正如《倾城之恋》中的白流苏说的,三十多岁的女人,往往有着反常的娇嫩,一转眼就憔悴了。而我,恰好目睹了她的娇嫩和风情万种。
那是株幼龄的白兰花树,枝干纤细,绿叶间藏着或青或白的花蕾,每天只开七八朵。人还没到门口,就捕捉到空气中若有若无的暗香浮动。白兰花香很特别,比茉莉花香幽静,比栀子花香素朴。修长的披针形花瓣,温润如玉的白色里透出一点点隐约的蟹壳青,像天边浅淡的月色。摘花最好趁露水,花瓣微微闭合的白兰花才适合别在衣襟。摘下的白兰花,仍是鲜活的,不知生死,在衣襟间慢慢地开一整天,香一整天。
经常,我们去的时候,阴影处的井盖上已放着七八朵白兰花。有人说,陶子,你家张师傅倒细心,花都替你摘下了。
陶阿姨咯咯笑着,他知道你要来,特地为你摘的。
哎哟,放着你这么个美人,他哪看得上我们。
张师傅我见过,是厂里的维修工,苍老矮胖,终日穿着深蓝的工作服。陶子是贸易公司的采购员,不大坐班,经常出差,总是天南海北地跑。
我和碧云站在廊沿下逗着笼子里的画眉鸟,她们站在院子里头挨着头,用针线或细小的别针把白兰花缀在衣襟上,偶尔嬉笑着互相帮个忙。陶阿姨也在她们中间,但不知怎么的,我竟看见她周围有一片小小的真空,她出不来,别人亦进不去。她打不破那层孤独和落寞,她亦融不进别人的热闹。
20出头的我,不大能够看懂,却被莫名地吸引。
他们一直没有孩子。但是都说陶子很能干,什么赚钱倒什么。她倒汽车,倒设备,还把厂里的下脚料收下来转手,赚取差价。也有人说,别人收的是下脚料,她收的未必就全是下脚料了。说的人总是表情暧昧,神色复杂。其实家属区里面早就流言四起,关于陶子一桩桩危险隐秘的恋情,以及因此得到的种种便利和机会。
白兰花花期很长,一直开到了秋天。再去时,陶阿姨会拿些出差带的特产零食招待我们,也会帮师傅们捎回一些时兴的丝绸布料,式样时尚的羊毛衫,首饰。
一些人喜悦地接过东西,推搡着付钱,走出门就开始交头接耳,脸上印着心照不宣的嘲讽。
我很怕她听见什么,紧张地回头看院子。她在给画眉喂水,踮起脚,提着纤长的腰身,象牙白小西装的下面,露出一截黑色蕾丝内衣。安之若素的,她在各色流言里自顾自美丽。
而她身后,白兰花开得恰好。冬天的时候,她搬去单位新分的楼房。红砖平房遂易了主。带着某种宿命般的暗示和指引,白兰花再也没有开过。
陶子阿姨说,外孙女都读小学了,她和张师傅每天的工作就是洗衣做饭,接送孩子。
(责任编辑:凌薇)
版权声明:凡注明来源“0517网”的作品均为本网原创作品,未经授权,请勿转载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