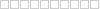□ 张素苇
小时候的茨菰生在屋后浅浅的淤泥塘里,抑或在水稻秧田的一头给它们留个“小床位”。它们的茎杆随秧苗一起茁壮成长,箭头似的叶子朝天空仰望着,却总是望不穿天空。它们开白色小花,似乎想表明自己纯情傲骄。我那会随父母去田里,会揪茨菰的叶子和花玩,玩不出花样,闲得慌,不三不四地就想搞破坏。
花落后,茨菰会不会像院子里那棵梨树一样结果呢?没有去向谁问这个问题,对于身边习以为常的事物,儿时的我并没有打破沙锅问到底。时近秋天,稻穗低头想快点让它们颗粒归仓,茨菰的茎杆也开始被秋霜勾勒出一道枯黄的线条,而真正的主角——茨菰却在泥土里,它们不知人间的季节就要入冬了。
茨菰实际上是母亲长着玩的,自然不急着刨回去,等到水稻收好晒干了屯好,大田的冬麦种下去,手头闲了,这才会挎着篮子扛着铁齿钩去把那两三行茨菰刨回来。长在秧田头的不会比长在淤泥里的高产,田地也早板结,刨了半天,总算是挎着半篮子七大八小的茨菰回来了。
家里剥茨菰这些事,只会交给父亲。冬天是他农闲的时候,某天,他依然双手插在袖笼里坐在草垛旁晒太阳,他的耕牛在慢慢嚼着干草。母亲把盛放茨菰的篮子朝他面前一放,说,别光顾晒太阳,也做点事。然后父亲朝母亲一翻白眼,还是抽手剥起茨菰来。我那会早溜走了,大冷天的,我可不干。
吃饭时,看着一碗干巴巴的滑烧茨菰,脑门就皱皱的。尝尝很苦。三姐说,和肉烧就好吃了。问母亲为什么不买肉。她说,买肉?钱呢?麦子要追冬肥了,化肥还没买。我和三姐吐了吐舌头,从此,对茨菰没什么好印象。
母亲都希望孩子吃得快乐。我小的时候,母亲只想着怎么把日子过下去,现在,我想着怎么享受,怎么把吃变得有意义,做食物时,常想着怎么做才美。我喜欢买小小的茨菰,小得可爱,用肥瘦相间的有皮的五花肉煸出油把它们烧得油亮亮软糯糯的,我儿子三四岁的时候,小小的茨菰,小小的嘴,一口一个,吃得好玩极了。
我有时上菜市场,看到菜贩摊上被清理得干干净净又圆又大的茨菰就心生欢喜,便会买上一些,回来弄几个切片和青蒜炒着吃。那片片茨菰吃在嘴里轻脆脆的,浸染了蒜香,打开了味蕾,也是下饭的好菜。
昨天我没有买人家剥干净的茨菰,我想自己剥茨菰的枯皮。剥茨菰也不是什么技术含量高的活,它那么小不适宜用刀,只要一枚硬币,便可轻轻松松刮干净表层的覆皮和黄色的锈斑。清洗的时候,我想起小时候的事,也是茨菰们小时候的事。想起父亲坐在草垛旁剥茨菰的样子,想起母亲对我的碎碎念,而今想来心酸又亲切。
用心做好一碗色泽鲜亮的茨菰烧肉,端到饭桌,催促正在玩“旅行青蛙”的儿子:快来吃你小时候爱吃的盛在碗里的“逗号”啊!他过来一看,有点嗤之以鼻地笑说:你还真的童真不减哦!
(责任编辑:凌薇)
版权声明:凡注明来源“0517网”的作品均为本网原创作品,未经授权,请勿转载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