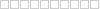□ 宋长征
家字的组成有两个部分,宝盖头代表低矮的屋檐,下面豢养着一头吭吭唧唧的猪,月光落在屋檐上,院子里的老椿树正在落花,一粒粒细小的花朵,代表时间在节气中凋零。我家的那头老母猪,无疑是一个伟大的母性,是村庄的功臣。很多人家的猪都是她的儿孙,所以日光晴好时常有一群猪在低矮的土墙外走动,蹭墙,似乎是来探视它们劳苦功高的母亲或外祖母。
我不能偏离太远,就像一说村庄的时候眼前就浮现出村子里的鸡鸭牛羊。我要说人,人才是一个村庄的基础,那些长大成人之后的人,无一例外都曾有过单调或美好的童年,都曾在孩子堆里,以自己的视角学习如何长大,如何在多年以后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。
过家家是一种属于孩子的游戏。二皮当爹,黑妮当娘,傻二最喜欢当大家的孩子。当然,有时我们也觉得无趣,谁也不希望以后有个傻二那样的孩子:鼻涕流过河,浑身脏兮兮。这时木圈就会出来重新推选,让傻二一下升到爷爷辈,坐在一旁的土墙上,不许说话不许动,像一个升天的牌位。二皮和黑妮的婚礼开始,有人嘴里发出滴滴答答的唢呐声,另有两人双手交叉握紧,黑妮坐在上面。二皮则被一个扮成高头大马的背起,晃晃悠悠。
大家齐声唱:呜哩哇,呜哩哇,娶了个媳妇一脸麻儿,瘸腿的姑爷骑大马。红砖墙,琉璃瓦,滴滴答答就到家。有人问——到家了吗?有人应——到家了。大家便会把新娘和新郎重重摔在地上,或者强摁着黑妮和二皮的头拜天地,碰响头,叽叽喳喳的笑声像一群慌张飞起的麻雀,窜进村东的小树林。
我看《红楼梦》,常会产生小孩过家家的错觉,黛玉,晴雯,薛蟠,宝玉,一干人等在一座夸张的院子里,不事生产,只觅风月。一直到后来读琼瑶,心中的疑问越来越深——他们难道只靠你侬我侬活着?他们难道不需要在河滩上开垦出一片庄稼地,他们的归宿莫非都会像红楼梦的结局,只落得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?
死亡总是来得突兀,没有预设好情节就呈现出悲惨的结局。二皮死的时候惊动省里的公安局,专门派人限期两个月破案。破旧的小院依旧破旧,除了死亡还散发出一股陈年的气味。二皮有一台联合收割机,昨天下午有人还看见他骑着摩托去县城,说是去车收割机上的零件,谁知夜里命丧黄泉。
血色弥漫,有关二皮与一个外乡女人的故事一经渲染,慢慢浮出水面。
外乡女人二十几岁,正是生机蓬勃的年纪。外乡女人的男人是木圈,有年木圈出门打工,两人在海边的一座城市相遇,领回家,简简单单举办了婚礼。几年后,有了孩子。有次打工回来的木圈听孩子说,二皮哥咬妈妈的嘴。一颗仇恨的种子由此种下。
我在叙述这些原本应该惊心动魄的情节时,常会被另一种冷静的力量引领,并非置身事外,或没有丝毫同情。一件事的源起,往往很早就在某处埋下伏笔,你想偏离预设的轨道,或跳出命运的诅咒,几乎不可能。二皮十八岁和黑妮结婚,黑妮比二皮大五岁,这在当时的乡村不算稀罕事,二皮也曾闹过,出走,最后还是被父亲强摁着头行了合卺之礼。
往事一幕幕浮现,过家家作为一个单纯的游戏,曾深深刻在我的记忆。我们每个人都不知道接下来的命运如何发展,就像那天凌晨时分从县城回家的二皮,把收割机零件丢在地上,沉沉睡去,粗大的木棒却已高高举起。
省公安在县城宾馆调取的录像显示,凌晨三时,二皮从宾馆匆匆走出,身后跟随一个年轻女子,坐上二皮的摩托车。说话有些磕巴的木圈,在闪烁的荧光屏里显得有些不真实,木圈说:我从水泥厂晚上八点下班,打她(外乡女人)电话关机。凌晨三时我早早起来去车站拉客,看见他们骑着摩托离开宾馆,后来我媳妇在一个路口下车,我就跟着二皮一直追到村口,在村外抽了几支烟。他不死不行——木圈在连续重复了三次这句话时眼里分明闪着杀机。
凶器,就是那根带血的木棒。
一段游戏的结束就是另一个游戏的开始,我在煞费心机的书写中捡拾起曾经的快乐,也陷入很多次痛苦的回忆。有句话叫人生如戏,我曾那么不相信一个人在世间走过抱着某种投机的心态,有时却又不由自主将笔触与生活对接。是巧合,还是某种暗示?如同极不明朗的暗物质在我们的认知之外,却主宰着人间悲喜。
(责任编辑:凌薇)
版权声明:凡注明来源“0517网”的作品均为本网原创作品,未经授权,请勿转载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