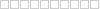□ 翟启荣
四九天里的几场降雪,给小城陡增了几分暮寒。周末下班后,抛开一切杂务,径直来到小区边上的澡堂,消消停停地泡个澡,身体和精神随之舒展开来。在氤氲的水汽里,我仿佛又回到了四十年前的万集老街,回到了老街上的那家澡堂。
老街不长,南北走向,入口处正临着由东向西通往洪泽县城的公路,这公路其实是草泽河的北堤。横跨草泽河的万集大桥,直对着老街的入口。入口的东侧是公社大院,西侧是上下两层、呈圆弧形的供销社大楼。供销社的新式门面继续向西延伸,正在形成一条新街。老街实在有些逼仄,街心用小块青砖铺就,两边的房屋店面大多呈现出斑驳的灰黑色。不过,正因为窄,因为旧,反倒更聚人气,更有市井味。在我这个头十岁的孩子眼里,那些杂货店、茶食店、剃头店、裁缝店、寿衣花圈店、烧饼油条铺,以及临街的老住户,无不有趣可亲。
澡堂坐东面西,门旁有一个烧开水的大灶台。里面分为两个区域,外边更衣,里边洗澡。更衣室又被一道帘子分为里外两间,外间大,里间小,票价相差五分钱。外间陈设一切从简,只在靠墙四周砌了不到一米高的水泥台子,上面铺了草席,墙上依次标着号头,浴客只能把衣服堆放在水泥台上。里间则装着亮堂堂的日光灯,过道两边对放着两排铺位,上面铺着浴巾,浴客洗完澡可以从容地躺着。过道上还放着取暖的炉子,不时有茶水供应,还有人递手巾把子。我和父亲与大多数人一样,每次都是把衣服脱在外间的水泥台上,洗完澡略微歇会儿,就得赶紧穿衣服。
浴池是常见的大小两个通池,大池子水温尚不太烫,小池子则烧得滚烫,小孩子根本不敢靠近。浴池里通常人很多,到了年根,更是人挨人,蹲都蹲不下来。我嫌澡堂里气不好喘,向来对洗澡不大感兴趣。每次刚洗一会儿,就开始玩两个浴池之间的隔板,玩别人搓背时枕头的木块,玩吊在浴室门后的木头墩子,有时甚至偷偷跑到更衣室里玩。于是,父亲赶紧把我抱回雾气弥漫的浴池,连搓带洗先帮我洗好,再抱到更衣室的水泥台上,一层一层帮我穿戴起来。临了,还不忘摸出“歪歪油”,在我脸上、手背上、脚后跟仔细搽上一遍,这才放我先出来找母亲。
父亲洗澡其实是泡澡,要在小池子里熥,时间要长。有时他会和我的某个伯父一起,边洗澡,边闲谈。一天早饭后,老街的墙角还积着残雪,两边的房檐上挂着筷子长的冻凌铛,父亲早早就和二伯父一起,带着我进了澡堂。浴池里只有几个人,光线从天窗上照下来,看得出池水很清。父亲和二伯父一边泡澡,一边竟扯着嗓子唱起了老淮调。你一段,我一段,或高亢,或低回。看着他们陶然欲醉的样子,我虽听不懂,倒也很开心。也是在那一回,父亲的一个熟人,笑呵呵地摸着我的后背,夸我养得像土脚头子,两头一样齐。还煞有介事地问:怎么养的?父亲连说带笑:一天刷五顿!那人追问:书念得怎么样?父亲道:学习标兵!其实,那时我也就当过两回“三好生”,奖状都贴在我家堂屋的山墙上呢。
澡堂门口的大灶台,每到傍晚便热气腾腾,人声嘈杂。晕黄的灯光下,三三两两的妇女、老人拎着茶瓶聚拢过来,有的还带着自家的孩子和狗。老街坊聚到一起,谈兴总是很浓,好些人似乎并不急着打水,水打好了也不急着走。最忙碌的是大灶台前那位驼背老头,他围着一副大围裙,时而朝各个茶瓶里灌开水,时而向几个大汤罐里加冷水,时而往灶膛里添稻壳,时而又从别人手里接过打水的筹子,忙得不亦乐乎。
每次我洗澡的时候,母亲就会加入大灶台边热闹的人群中。她通过熟人,不厌其烦地打听我洗澡、穿衣的每一个细节。当我跑出澡堂大门时,不用在人群里寻找,母亲早已笑吟吟地紧挨着门口接我了。她明知我不饿,还总是带来吃的东西,有时甚至从桥南饭店买来喷香的卤兔子头,塞到我手里时,还热乎乎的。
(责任编辑:凌薇)
版权声明:凡注明来源“0517网”的作品均为本网原创作品,未经授权,请勿转载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