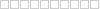□ 郭虎
我们家的亲戚平常也不怎么联系,没事的时候嘘寒问暖之类的很少。3月21日(农历二月初五,春分)傍晚的时候,我突然接到小舅的电话,顿时一怔,果然,小舅说,你外婆“走了”。语气还算平静,说年纪大了,九十六岁寿终正寝。
早在上世纪1991年,我就写了篇散文《外婆》刊登在《莫愁》杂志上,那时候我才24岁,多愁善感的文学青年。那篇文章后来我都不怎么示人,因为那个年纪还不成熟,字里行间都能挤出情感的汁来,我的个人散文集出版的时候,都犹豫着要不要收录进去。算起来,我那篇文章发表的时候,外婆是70岁,古稀的年纪。上世纪八、九十年代,社会涌动着朦胧诗潮,我也会写一些不明不白的东西自我陶醉,一发表了就有诵读天下的热望,但从这篇散文发表后,我就告别了青春写诗的热情季节,开始了散淡的散文写作,所以,这篇《外婆》于我来说也有一定的象征意义。
外婆长寿,她终于等到我也快老了,因此,这些年我都会在春节前去看她一次,听听她絮聒。早前,我一去,她还能拄杖站在门口,过去的一些邻居会围拢了来,她会大声炫耀说,我外孙来看我了。还把我的名头说出来,让别人啧啧称赞,她会满足地执着我的手把我往家里拽。再后来,她渐渐行动不便了,平时她的长孙媳妇会照顾她坐在门前的藤椅里晒太阳,年轻人当然不会陪她说话,她就把头抵着手杖等太阳下山。我去的时候,她会一直拽着我的手,问许多事情,问完了,就讲从前的事,一遍遍不停重复,和妯娌间的不和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也还记得清楚,总说,我就不死,我不死在她前头。我就笑,会大声地说,好啦,都几十年前的事了,我要走了。一见我要走,她会哭出来,使劲拽着不松。
我还记得外婆过九十大寿的时候,小舅舅把她接到城里的酒店,办了好多桌,那时候她已经耳背,被大家安顿在台前中间的椅子上,小舅舅是中学校长,他站着致辞,她也听不到讲什么,但脸上总是保持着笑意,大概晓得大家的意思,怀里是晚辈献的一捧鲜花,衣着整洁,头发也绾得整齐。大舅歪头笑着对我说,你看,身体比我还要好。
每年的年根我照例去看她,大舅也照例说,身体还好。但我还是觉得她的精神一年不如一年了,后来眼睛也浑浊起来,已经不大能看得清来人,我去的时候,大舅会大声地告诉她。但意识还是清楚的,还是会说起妯娌的不好。我明显觉得到她身体越耗越轻,骨瘦如柴,力气也小了下去,假牙拿掉了扔在旁边有水的碗里,一个人睡在一间屋子里,我感觉她身体的温度抵御不了寒冬,大舅说,有电热毯。
今年过年前,我买了许多开水冲了就能吃的东西,有奶粉、芝麻糊、软糕点等等,驱车去看她,嘱咐表弟媳平时可以给外婆加点营养。外婆一人静静地躺在床上,问谁呀,谁呀。大舅如往常一样大声地告诉她,她突然哭起来不能抑止,我因感冒初好,并不敢久留,怕她这样的岁数万一被传染了抵御不了。她看我又是来去匆匆,就把瘦瘦的手伸出被窝紧握住我的手不放,没牙的嘴瘪下去,大哭,大哭。
总以为跟平常一样的,但在年后的春分那天,大舅事后好几遍地重复说,中午还吃一点饭的,也是清醒的状态呀。下午本准备去打麻将的表弟媳发现了异样,连喊了人来,就已经“走了”。
外婆的一生,跟她这个年纪的人一样,大都经历了苦难。只是她的长女,也就是我的母亲考上学校成了家庭的骄傲,然后又早早地过世,成了她长久的心痛。她的丈夫,也就是我的外公早年是地下组织成员,然后又莫须有地被捕,在新疆直到晚年才平反归来。这些都构成她劳碌一生的坎,连她自己晚年也惊诧能活这么久。
这世上本就没有什么永远。只是再到年根,外婆家那里必定少了一个等待。
我后来一直想,外婆在年前一定是在跟我握别,只是她哭得那样的不能抑止,这让我心痛。
(责任编辑:凌薇)
版权声明:凡注明来源“0517网”的作品均为本网原创作品,未经授权,请勿转载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