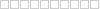□ 朱文颖
“从前在乌斯国有一个人。这人完全正直,敬畏神,远离恶事。他的牲畜有七千只羊,三千头骆驼,五百只母驴,还有很多仆役。他比所有住在东方附近的人都更有气派。”约伯的故事就是这样开始的,他有幸心满意足直到上帝向他举起了手,用麻疯病打了他一下。以便他从麻木的舒适中醒来,饱受精神之苦。
当然,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有约伯开头时的那种幸运,倒是约伯后来的遭遇,与它不期而遇的可能性会更大些。比如说,《戴女士与蓝》里的那个“我”,有一天,他发现自己穿着鱼的外衣,莫名其妙地躺在异国他乡的大鱼池里。这还不算,到了后来他又发现,不管他费多大的劲,把外衣脱掉以后,他却仍然还是一条鱼。
这固然是件让人伤心的事,当然,即便是“绝望”或者“悲剧”,每个人的认识也都是不同的。就像前几天,我看《法斯宾德的世界》,里面有这么一个细节。1977年的一次谈话里,克莉丝汀·汤森问法斯宾德:《库斯特婆婆上天堂》拍了两种结尾,一种是库斯特婆婆被枪杀,另一种是库斯特婆婆爱情完满、安全回了家。汤森问法斯宾德自己喜欢哪种结尾?法斯宾德说他喜欢“安全回家”的版本,因为他觉得那更悲惨。
这是一种惊世骇俗的想法。一般来说,这样的极端是很少有人能做到的。但是,如果照这个说法,小说里的“我”像一条鱼一样存活于人世,痴情的女孩子跳楼而死,而戴女士呢,也是不死不活的,连自己是谁都不肯承认……这里面谁更悲惨些,还真是不好说。
不长不短,小说写到今天也有八、九年了。而“什么是小说”这个问题,却是需要重新来认真认识的。什么是小说?如果就技巧而言,我现在认为应该是某种智力游戏。小说的内部一定存在潜规则。而要做到随心所欲却不逾矩,却是要从基本的功夫做起的。也就是说,要从无技巧做起。另一方面,更重要的方面,从小说的大处而言,则是智力完全无法抵达的。非但无法抵达,或许还会成为阻碍。因为归根到底,此事关涉心灵——这是骗不了人,更骗不了自己的。
在当今的中国社会,生活不容易,写作其实也是艰难的。我们的四周是一片意义的混乱与荒漠,对错模糊,善恶是没有明确标准的,就连标准的本身也被模糊与取消了。时代急剧变化,人心浮躁,没有人愿意为心或者灵生活。任何企图抓住实在之物的努力,结局往往是痛苦。从这个意义上看,我认为真正的小说家,他应该具备一种特殊的智能,强大的心灵。他的手里掌握着破译世界秘码的一把钥匙。倒不是说,有了这钥匙,世界的神秘之门便为你一扇扇打开,各种问题迎刃而解……恰恰相反,门的终端往往通向失望。因为这门一定是无可穷尽的。就像2002年9月17日开启埃及金字塔那扇神秘石门的结局——考古学家们发现,在石门的后面,还有另一道石门。
现在就让我告诉你,我理想中的小说家的姿态:
其一,他其实从来不认为,神秘石门的后面就有一个截然的结果。
其二,在面对九百九十九道石门过后,他仍然双膝跪地,泪流满面。
是的,圣灵从来存在,虽然,我们谁都没有见过它。
写作生涯走到中途,对于文字,对于生命,多了感慨与发自内心的敬畏。我希望自己沉下来、缓慢下来,扎实起来。生命开始展现它真实的面目与状态,帷幕渐次拉开……
(责任编辑:凌薇)
版权声明:凡注明来源“0517网”的作品均为本网原创作品,未经授权,请勿转载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