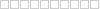我对木梳的记忆,也是从母亲身上开始的。
在我们家里,木梳是和母亲一起醒来的。准确地说,太阳还在五峰山上睡着,庄稼还在田野上睡着,鸟儿还在树枝上睡着,一村人还在土炕上睡着,而母亲已经起来了。她的身子,应该在每个黎明之前,最先被一丝亮光照耀过的。她的手指,在触摸每个日子的时候,也是最先被一把木梳拉住的。
我想母亲的每一天,都是从头上开始。
开始用一把木梳,把一夜的睡梦梳理出去,也把一天的精神梳理出来。那时侯,她是坐在靠窗户的炕沿上,借着透过窗户纸的亮光,梳理自己的头发的。母亲一生的清爽,应该来自每天晨起的梳头。你想,一丝透天透地的晨光,一缕润心润肺的晨风,一声入耳入骨的晨鸣,和着一把木梳的齿痕,在母亲的头上移动着。这些藏在大自然身上的东西,不仅会贯通母亲的血脉,也会在她身上,唤起一些劳动的激情。
梳好头的母亲,从炕上整洁地下到地上,就再也不会停止一天的走动。
她多数是在院子里,梳理着生活里的农事:纺线、织布、缝衣、晒粮。
她也要走到田地里,梳理着季节里的农事:种豆、割麦、斫谷、打场。
而把身子沉浸在二十四个节气里,母亲的一生,就是在土地上为我们梳理日子。她在劳动中付出的是什么,这把天天走进她头发里的木梳,是最清楚的。因为只有它,能零距离地走近母亲好看的头发。我也发现,这把和母亲一起处在岁月里的木梳,不像母亲的脸上和身上,开始有了一种沧桑感,而是越来越光亮。
那些被母亲握出汗味的木纹,也越发夺目了。
我想那是母亲身上的气味,让一把极其原始简单的木梳,得到了很好的浸润。就像我和姐姐,还有憨厚的父亲,天天从母亲身上得到的滋润一样,它会使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部分,在蓝天下的田野里,像庄稼一样健康生长。
后来我明白,那把木梳是母亲用来缓解身上的疼痛的。
我懂母亲,一生是一个精神清爽的人,也是一个精神愁苦的人。作为一位女人,她的负重是双重的。她有一个让她一生不开心的娘家,为了那个破败的家,她操碎了一颗属于女人的心。她守了一辈子的我们的家,也是她用了一生的时间,像梳她的头发一样,一天天梳完整的。在马坊这块土地上,她被贫穷折磨过,被乡俗折磨过,也被亲情折磨过。她瘦消的身体,承受过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。比如大姐,因一次意外从树上掉下来,被摔成了一个病人。她的骨头没有受伤,但精神受了很深的伤。她拖累了母亲好多年,是带着病身子出嫁的。我不能想象,那个时候的母亲,内心的深处有多疼?或许是上天感念她的善良,竟让大姐的病出奇地好了。还有二姐,一个言语不多的女子,嫁给了一个让她吃尽苦头的人家。我的印象里,姐夫和姐姐在这个人口很多的家庭里,是一对受苦人。她的生命的路程太短了,短到母亲还健在时,就离开了这个进错门的家。记得埋二姐的那天,母亲在我单位的一座房背后,一个人哭了一场。我们回来时,看见她手握一把木梳,心绪很乱地,有一下没一下地梳着头发。
这与我记忆中的动作,完全不一样。
这时的木梳,以及木梳的移动,是对伤痛的一种掩饰。
再后来,就是母亲去世的那天,我是被一阵梳头声惊醒的。很多年了,木梳在母亲头上移动的声音,已有些淡漠。我睁开眼睛,看见母亲背对着我,正在仔细地梳着她的头。木梳在她稀疏的手里一上一下,穿过头发的丝丝声,听得我有些悲伤。那些光亮的木梳齿,像木匠们手里的锯子,从我身上狠劲地锯过。我平静的心里,突然有了生命中最疼痛的感觉。我以为这是平常的一次梳头,没想到这是她留给我的最后一张剪影。
我是记着母亲梳头的动作,送走母亲的。
也是听着母亲梳头的声音,送走母亲的。
那场纷纷扬扬的大雪,护送母亲的遗体,上了封侯岭后,穿过两道深沟,下了碾子坡,进入我们村。一个人的一生,就这样在土地上走完了,我一直思考:她把最后的日子,也要留给白发挽洗?也要木梳朗诵着休止?作为她的儿子,我希望把她放在那个梳头的场景里,供一颗心时时记忆。
因为穿梭的木梳,是我接近母亲时最可靠的物件。
木色的冷清,木纹的灰暗,不会磨损它——从乡村的早晨,雨露一样带来母亲身上的气息。我要用一生的时间,记住残缺的齿痕,印在母亲单薄如麻的身体里,也是马坊的齿痕。
我不说时间的天空,把多少重量压在母亲的头上。
只想告诉你:她一生用木梳,从头缓解乡村的疼痛。
(责任编辑:凌薇)
版权声明:凡注明来源“0517网”的作品均为本网原创作品,未经授权,请勿转载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