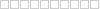□ 宋长征
天灰扑扑的,一条沟渠通向不远处的小集市。省略了父亲和母亲,在我的记忆里,童年几乎是我一个人的,家里的每个人都在忙,都在挣命,无暇顾及一个到处游走的野孩子。好像是秋天,记忆中极不容易忽略的多是秋天,秋天天高地阔,秋天长风万里,秋天的萧索正好符合我沉默讷言的秉性。扒开枯萎的茅草,沙质的土壤很容易松动,有钱,一分两分,一毛两毛。我不知道小时候为什么总做捡钱的美梦,就像此时,难以压抑心中的激动,有了钱就可以买好看的画册,有了钱就可以买好吃的食物,还有什么是钱不能解决的问题?那时的我还真的没有去想。
一个乡下孩子最大的梦想就是别人家的孩子有吃的有玩的,自己也要有。我没有,我只有梦。二哥在村东烧制陶盆,利用工作的间隙给我捏制土陶罐儿,下面有腿,上面是身,身后有尾巴,头上有鼻子,上下粘和,就成了一只小猪形象的储钱罐儿,用树枝画出耳朵、鼻孔、眼睛、嘴巴,憨态可掬。我也憨态可掬,把烧制好的土陶罐儿拿回家里,放在床头上,一分、两分,储蓄着有钱人的美梦。直到今天,我仍觉得童年的那只储钱罐空空荡荡。
我不可能有什么储蓄,母亲把鸡屁股当银行,每逢集市,提上几十枚鸡蛋去卖,卖了买回油盐酱醋,也就换回了一家人简单的日月。我上学用钱,母亲就说:“记着,拿小本记着,看你到底花了多少钱。”说实话,这是我最反感的一句话,隔壁的合子娘,也拿这个说事:“你看看你娘,老跟孩子说什么钱啊钱的。”我就觉得合子娘对,就觉得合子是村子里最幸福的人,合子要买什么东西,只要一张嘴,合子娘就会大大方方地说:“乖啊小啊,我给你拿。”我没想当时的家境,母亲一个人掌管着那么多张嘴,父亲治病也要钱。
我上学,建立在二姐、三姐不上学的痛苦上。大哥、二哥出了远门,三哥当兵,大姐嫁人,母亲就说女孩子上学没啥用,早晚嫁人。钱的诱惑,主要来源于那些馋人的小食物,玉米棒、瓜子、又酸又甜的橘子水,想到就让人流口水。就撒谎,说买笔、买本,小心翼翼把钱捏在出了汗的手心,出校门,在小商店买几块糖、一毛钱的瓜子。那个香啊,至今不散……
我爱钱,我相信很多人都爱钱,要不,不会有那么多人三更睡五更起,颠簸在路上。在金州,一间不大的小棚屋,我居住了51天,刚开始还好,在汽车队装卸水泥,一袋100斤,上上下下,一天要搬运几十吨,衣服结成块,鼻涕结成块,晚上躺在床上咳,像一个患了哮喘病的老年人。调度看着不对,说我身体单薄,可以到汽车队上班,每天查看轮胎,看看油箱,就是刚开始工资有点少,150的工资,吃了上顿没下顿。一个中意我的女孩来做客,外面下着雨,人不留人天留,吃了一顿烧土豆。女孩说:“爱情是什么?”我苦笑:“爱情就是烧土豆。”去你的烧土豆,从此后那个女孩再也没来找过我。
我可能是延续了童年的梦,小时候在茅草窝里能翻捡到一分两分、一角两角的钱,所以落下一个剃头匠的结局。这也没什么不好,不偷不抢,顾客上门,一通洗剪吹,照镜子还算美观,给钱走人。一元、两元,集腋成裘,日子倒也宽裕。我又抽烟又喝酒,烟是弹指间尽显将军本色的“红将军”,物美价廉,一篇文章下来也抽不了几支。酒有点讲究,价钱勿论,但一定要高度粮食酒——我不酗酒,跟小说家、散文家、诗人皆有觥筹交错,能让我喝趴下的还没几个。
我最大的开销在书上。上了一年高中,别人没见过的文学刊物我也订,钱从哪儿来?当然是撒谎从母亲的鸡屁股银行骗来的。
日子渐渐好起来,日子总会好起来。我相信自己,在家里种田能成为一个及格的农民,给人剃头能算得上一个合格的理发师,展开纸来写文字,能把自己想要表达的情绪传递给阅读者。这是一个不小的进步,至少我没有辜负生我养我的父亲、母亲,至少我没有辜负脚下的那片土地。
(责任编辑:凌薇)
版权声明:凡注明来源“0517网”的作品均为本网原创作品,未经授权,请勿转载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