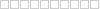□ 钱红莉
年画的本源,起于民间,活于民间,离不开胖娃娃怀抱锦鲤图。娃娃不仅胖,而且一律男孩,白赤条的身上系一只大红的肚兜,怀里的鲤,是锦鲤——鲤,这个鱼种擅长逆流而上,于关键时刻,飞身一跃,这在民间无形里就有了一种象征,逐渐演化为“跳龙门”之意。中国的民间最重视什么?是繁衍生育。咧嘴大笑的男娃娃作为最恰当的代表,人们对于他的期望,是长大成人后的鱼跃龙门。
除了繁衍生育,民间还关注另一件事情,那就是长命百岁,所以,年画里断然少不了这一项,分别是“松鹤延年图”或者“寿星托桃图”。前者的画里有松树和白鹤——松是万年的松,也叫万年青;鹤是仙鹤,红嘴白足,不老的,终年飞翔在“有”与“无”之间——这样的画适合挂在厅堂,我们也把它叫作“中堂”,所谓贴中堂就是贴这种松鹤延年图,每年贴的都是新买的,年年如此。中堂左右再配上一幅对联,端正,肃穆,下面摆了花几、八仙桌和木椅,自腊月二十三小年开始,大人将祖先们从天上请回家,每天早晨用餐前务必呈上三碗清粥拜祭,以示尊敬。孩子们立在桌前,双手合十,默默等一会,偶尔,眼光越过碗内袅袅飞升的热气直达壁上的中堂,所有的祖宗仿佛齐齐幻作了青松、仙鹤。
在我早年的记忆里,每一家祖先的面貌几乎是大同小异的,他们都化作了青松、白鹤,一齐被悬挂在堂屋。至于“寿星托桃图”,一般贴在厨房——民以食为天,食为生命之本,一个人若要长寿,当然离不开吃食。那么,就少不了拖着一把白花花长胡子的宽额老爷爷,左手拄着深枣红色松木拐杖(拐杖同样做成人形,上面是一个生得富态的老寿星写意,以审美的眼光看,简直是一件上品木雕),右手托着一只巨大的红桃,笑容可掬地站在厨房的墙壁上。与之相对应的,则是锅灶上粘贴的红脸灶神,它凶神恶煞,不得小孩子喜欢,甚至有恐惧,不愿多看一眼。早年,我一直不解——为何中国的神仙鬼怪大都生着一副凶悍的脸,后来慢慢明白,那是有着震慑作用的,它震慑的是人心里的小奸小坏,让你看着它们的那张脸就已溃不成军了,谈何作恶多端?西方的宗教人物则迥然不同,它们的形态一直是宽容温和的,甚或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受难形象,一律以慈悲为怀,意在感化,让人生忏悔之心。人一旦有了反省之心,还谈得上作科犯奸么?同样是教化,在东方与西方,则达到了冷暖两极。
与凶神恶煞的“灶神”相比,“钟馗嫁妹”简直可亲得多——尽管在孩子们眼里,钟馗是那么丑陋凶悍,他眉毛倒竖,眼白频翻,双刀在握,迈出的步子像醉汉,东倒西歪,高抬慢走的,比起哥哥的鲁莽,妹妹则显得弱质些,即便她的脸被闷在红盖头里,听大人们言,也着实不大好看。相比起主角来,孩子们最爱的则是那些抬着嫁妆的老鼠们,它们一个个生龙活虎的,幸福感、喜悦感溢于言表,妹妹的嫁妆,被它们抬着,扛着,背着,一路乐不可支,吹吹打打,浩浩荡荡,如开赴前线的士兵,穿红着绿,直把人间喜事演绎得锣鼓喧天。
腊月,正月,正是民间嫁娶的好月份。“喜鹊登枝”的年画,终于派上用场,新房里少不了张贴它的位置。喜鹊与乌鸦,原本都是一身黑羽的鸟类——为什么喜鹊一跃而成为人类的坐上宾,乌鸦则如此不招人待见?——乡下人的房前屋后都植有大量树木,一旦喜鹊停歇在树上歌唱,人们会预知,那家该有喜事了……若是乌鸦呢,主人快快将它轰走,心底还隐隐埋着不痛快。鸟儿原本与封建迷信扯不上关系——在西方的神话传说中,乌鸦就是一种不祥的鸟。它喜欢火,而且擅长衔起正在冒烟的燃烧物,放在人们的屋子里,时时燃起一场冲天大火……中国人对于乌鸦的不耐终于在西方神话里得到了有力的印证。
“喜鹊登枝”里的喜鹊,登上的都是红梅,火一样热烈的红梅开得正酣,大红的光芒映照在喜鹊身上,有淡金的幻影。报喜鸟落在红梅上,不就暗合了抬头见喜一顺百顺的意思么?到这里,不能不提中国人的生活智慧,同样是祈福,用绘画来表现,向来多姿多彩;若用方块字的话,更加层出不穷——仅仅“福禄安康”四个字里,就包含着一切美好的祈愿:生活安宁,身体健康,福财双有,到了这一步,人还祈求什么呢?
什么也不用祈求了,于是想起来挂上红灯笼,贴上门联、门庆——新年的风一吹,花繁柳绿的门庆肆意飞舞,人们进出于门扉,红纸屑借着寒风一点两点,飘下来,正好在黑发里落脚,拂也拂不脱,索性让它们粘着去,也不碍事的,反而添了喜气——话说了几个来回,还是落在了这点“红”上,中国人对红色的衷情由来已久,连少女的黑发上,扎的都是红绳,喜被也是红线缝上的,红包也是红纸做成的,还有一响冲天的爆竹,同样由红纸层层叠叠包裹着,惊天动地的霹雳后,散下一地红纸屑,小孩子踩在上面,松软喜气,他们不时从怀里拿出从家里偷来的零散爆竹,趁人不备,点着,裂帛一声,炸得魂飞魄散,但,转眼,心神也就定了下来,到底还是那一抹红,给人以暖意……
(责任编辑:凌薇)
版权声明:凡注明来源“0517网”的作品均为本网原创作品,未经授权,请勿转载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