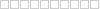□ 余萍
太阳可以把老屋晒黑,风可以把老屋吹旧,一场春雨也可以让墙缝和屋顶的草籽发芽,但谁都改变不了老屋在我童年留下的特殊印记。
老屋陪了我十年。我的十年光阴,坐在老屋各种各样的声音里,老木门的嘎吱声,门檐下燕子一家的唧啾声,老屋墙根土鳖子、多爪虫们来来往往的脚步声,蚂蚁触角的碰撞声,院子里青竹的拔节声,花草在暗夜里私语的窃窃声。这些声响温暖了我的记忆。当然,也有的记忆,如针,深深扎在我心上,譬如一夜一夜的风雨。
老屋门前有个草堆,夏天堆的是麦秸秆,秋天堆的是稻草,轻风淡淡过,满院草屑香。不过,麦秸秆的香是昂扬的,浓烈的,有盛夏阳光的味道;稻草香则沉郁些,内敛些,有秋风的况味。草堆里的草,有时会拾掇一些覆上漏雨的老屋顶,让我们一家暂避一时雨淋,更多时候是舍不得的,没有了草,烟囱就没了炊烟。
幼年雨水似乎特别多,一下就是三五天。屋顶的草腐烂了,若不能有新草及时铺上,一旦下雨,屋内便是七漏八淌。裂缝的墙体,更是肆无忌惮地任雨猖狂。
喜欢下小雨的时候,屋内和唱似的滴答。母亲叫我拿一个脸盆放在漏雨的地方,我照做,然后站在一旁,看雨滴答下来,伸手在脸盆上方接,雨滴一点点洇湿掌心,再从指缝漏下,落进盆里,凉意沁心。雨点大了,滴答声会跑调,更觉有趣。
某个夜半,突然被父母急促的唤声惊醒,闪电的瞬间,看到老屋面目狰狞扭曲,内心一阵恐惧。父亲斜身以肩死抵一根木棍,母亲扶另一根,两根木棍交叉支撑北面那堵歪斜很久的墙。裂缝如蛇,暴雨、闪电、雷声划过蛇身挤进老屋。地面积水漫过脚面,水里排着盆盆罐罐,连灶上铁锅也漂在地上。母亲急促的呼唤,是叫我和哥披上塑料纸站到门外。
深夜,一块塑料纸遮不住我们兄妹,我们在雨里撕扯着,全然不知父母在摇摇欲坠的那堵墙下想了些啥。
天明的时候,老屋温和了许多。傍晚,天彻底露出笑脸。夕晖斜洒,风慵懒地在门边溜达,门前泡桐树上的喜鹊归巢。丝瓜架下,瓜和花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,小鸡仔们聚在窝里絮叨着一天的见闻。我躺在院里凉床上,仰面看天,云闲闲地过,鸟轻轻地飞。暴雨里挣扎一夜的老屋也许太疲惫,睡着了。梦里,它也在梳理昨夜的惊惧吧。我不敢去推门,生怕嘎吱一声,惊扰了老屋,惊扰了它难得的酣梦。
老屋见证了父辈的苦难,也记录了属于我的无邪童年。老屋真的太老了,我能记事起,它就如垂暮老者佝偻着背在岁月的风里残喘。
后来,老屋在父亲手里翻盖成了红砖青瓦房,又在我哥手里豪华成了三层乡间小别墅,再后来,被开发商克隆成面目统一的商品房。
现在,老屋彻底不见了,那时的光阴也淡了。但是,人脑有时就跟抽屉一样,一旦抽开,淡去的光阴依然会再现。磕磕巴巴的泥土里走出笑来,冬日檐下的冰挂吮出甜来,老水牛的扁嘴巴嚼出一个又一个季节来……
偶读海子的《浪子旅程》,也想学他,头插鲜花,在故乡的天空下,在老屋的门前,沉默寡言或大声谈吐。可惜,我只能在纸上,用黑笔涂鸦两个字——“老屋”。此时,那个墙头长草,墙缝漏雨的土墙茅屋便会逐渐清晰起来。屋前一架丝瓜,架下蜗牛爬着,瓢虫飞着,蝉叫着,瓜吊着,我的鼻腔里也回旋起属于老屋的草木香气。
(责任编辑:凌薇)
版权声明:凡注明来源“0517网”的作品均为本网原创作品,未经授权,请勿转载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