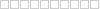温醇的小南风一吹,倒春寒不再来了,冰凌霜冻也化成了绵绵细雨。眼瞅着就入了夏。
门前,白累累的槐花透着香,树上黄里透红的樱桃吃个十来天就没了接续,而杏子、李子、桃子都只挂果还没成熟。田地里,一片片黄澄澄的麦子芒刺坚韧,一垄垄挤挤挨挨的油菜籽粒饱满,布谷鸟天天在村前屋后“阿公阿婆,割麦插禾”反复地鸣唱,看形势真的该开镰收割了。
对于乡村农户来说,午季是顶顶重要、顶顶紧张、顶顶繁忙的一个季节。小麦、油菜籽的午季收成,关乎一家老小的粮油,关乎一年的日常用度,关乎乡邻亲朋的交往开销。黄金铺地,老少弯腰。抢收抢种的五月,乡村四处弥漫着针插不进雨泼不进的忙碌气息。
五月的天,孩子的脸。雷雨阵雨暴风雨说来就来。一旦麦穗脱粒落了田,菜籽过熟涨了荚;或者割下来的麦子油菜,遭雨运不出,就白白耗费了百多天的辛苦与心血。还有,下秧、插秧、点玉米、播黄豆、种红薯,也一刻不能耽搁。假如误了时机误了季,就荒废了大半年的好时光。因此,一到午季,农家人便男女老幼齐上阵,全心全力投入到这场抢收抢种的战争中。收了油菜收了麦,还得继续抢种水稻旱粮。
对于缺劳力的家庭,一到午季就犯愁。譬如我们家。父亲连带我们姐弟俩只当一个劳力,全指望母亲晒日头顶月头地连轴转。父亲在镇中学教书,兵头将尾只落忙的尴尬角色。“庄稼误了是一季,学业误了毁一生”,是父亲常挂嘴边的口头禅。“把一季庄稼耽误了,去喝西北风还是秧田水”,每每被母亲抢白。
真羡慕劳力多的人家,那干活真叫麻利。早晨还整畴整垄的麦子、油菜齐刷刷地挺立着,可到了晚上,就变成了整堆整垛的麦粒、菜籽;昨儿个还整亩整片光溜溜的水田旱地,今儿个就已横竖成行左右成线的播上种、插上苗了,看着都瓷实。
终于盼到三天忙假。天刚麻麻亮,连鸡鸭都没醒,父亲母亲就早起拿了筐担、镰刀就出门了。姐和我留家烧菜递饭。跟着母亲到过我们家的水田和旱地。水田近,在田洼村;旱田远,在距家三里地的民族村。先前几天,母亲已请二舅帮衬着把旱田里的油菜晒干扬尽装进了仓,剩下来两块田的麦子等着收割。
送稀饭馒头到地头时,父亲母亲和请来帮忙的郭侉子弟兄都在弯腰收割。一大片麦子割倒在田地里。我和姐把倒伏的麦子打成垛,一小捆一小捆地搬,连拖带拽到埂上。母亲不时回头:没劲就歇个脚,不要硬搬。一天下来,手上腿上胳膊上都被麦芒扎出了血印,浑身疲乏得说不出的滋味。
两天下来,我们跑腿打下手的都懒得挪步,不知父亲母亲如何抵挡。总看见他们为挑麦打垛、拖车推车争来抢去,似乎精气神挺足;可背地里,又会各自反捶自已的腰背,连吃粥拿饼也懒得起身。
一年年的午季,在欣喜和劳累中一晃而过;一年年的播种与收获,在慌慌张张中悄悄进行;一茬茬庄户人,会否像那些庄稼一般枯荣更替?
午季,是藏在我记忆深处一个不醒的梦。
(责任编辑:凌薇)
版权声明:凡注明来源“0517网”的作品均为本网原创作品,未经授权,请勿转载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