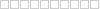二十多年前,我在淮阴工学院读书。那时的工学院还没有升格,叫工专,位于北京路,属三年学制。学校不算大,五个系的规模,只有两座宿舍楼。读到大三,我们的宿舍搬至北楼310,六层公寓中最佳的楼层。这似乎已成了学校的一个传统安排,从楼层的位置能够看出学生资历的深浅。那是一幢老式的楼房,宿舍窗外还砌了阳台,仿佛突破钢筋水泥振翅欲飞。闲暇时,我们可以翻过窗子到阳台上透透新鲜空气,不过很难晒到太阳。和北楼相隔十余米,是女生住的南楼,它不容商量地遮住了阳光,只在黄昏时分才斜斜的、懒散的挤进几圈红晕来。
在这样简陋的空间里,我们吃饭、学习和睡觉,偶尔举举哑铃、清清嗓子,有时也一齐扯高音量同四楼或五楼六楼往下倒水的学弟们争吵,或趴在床上一边听收音机里的校园民谣,一边给女孩子写信。虽然隔着一段距离,但南楼的燕语莺声,还是会时不时地穿透空气,钻进我们的耳帘。这些声音,常令我们的心躁动不安。阿骆曾在秋天的某次晚自习后,用望远镜仔细窥视过那间窗帘没拉严的女生宿舍,后来被谁告发了,挨了女班主任的狠狠批评。
有一件事让我们不开心。310宿舍的对面不是宿舍,是卫生间。那时的大学宿舍,远不如今天这么讲究,一个楼层就东西两个卫生间,偏巧东面的正与我们对门,就总有一些浑浊的气体不邀自到地混进屋来。宿舍管理员在每周一次的例行卫生检查时,总给310亮红灯,为此,气质逼人的女班主任多次亲临指导卫生。这很令人伤神。那时我们公费生每月可领到32块钱的大学生补助,由膳食科折换成六十四斤饭票发放,但如果宿舍卫生一月亮两次红灯,就每人扣十元。其实我们真的很努力了,甚至在床铺下划一道白线,将鞋袜一律整齐地排放在线内。我们向管理员解释,屋里的怪味是从对面厕所飘过来的,他不予理睬。大家又联名向总务处递交了一份“关于北楼310屋内怪味的客观成因”的报告,亦未奏效。最后,八兄弟不得不坐下来,慎重地研究如何真正解决问题。最后,大家一致采纳了舍长大周的建议,即每月按时送两包茶花烟给爱抽烟的管理员。四块五一包,两包九元,平摊出去,一人一块一毛多一点。效果还真明显,从那以后,北楼310的卫生很少再亮红灯。
时光在这些琐碎中悄然流逝,只是年轻的我们并不太懂得珍惜。毕业典礼后的那晚,系里安排会餐,大家都喝了啤酒,包括女生,会餐结束时集体起立高唱《毕业歌》。然后,系领导和各班班主任到男生宿舍陪学生打牌,他们怕情绪高涨的我们干出砸玻璃之类的事来。将近凌晨一点,老师们困了,走了。想着明天就要各奔东西,不知何时才能再见,我们谁也睡不着,三五一伙地聚在那儿聊,发誓几年后一定要做上科长或是经理。那时的我们,是那样的单纯,对外面的社会心存近乎完美的遐想。
大概两点多,南楼突然传来一阵尖细的哭声,这哭声,搅得我们心里也直往外泛水。而后,大周从窗口翻到阳台上,抱着吉他弹起《友谊地久天长》,我们跟着跳出去,大声唱起来。南北两楼沸腾了,有人“哦哦”叫好。女生们打开窗户,倚在窗口和唱。一曲终了,大周吼着嗓子嚷:来一首《吻别》吧。那是一首刚刚流行的歌。那个凌晨,在吉他声里,北楼和南楼开始“吻别”,到后来哭声一片。哥们胡海翻进宿舍,用刀子在雪白的墙上刻下给未来学弟的箴言:莫等闲,空悲切,白了头。最后郑重其事地署上大名:胡海到此一游。
(责任编辑:凌薇)
版权声明:凡注明来源“0517网”的作品均为本网原创作品,未经授权,请勿转载!